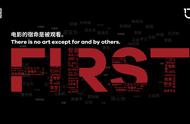 "
"作者 / 曹樂溪
閉幕前一天,閉幕片沒了。
2019年電影市場最大的攔路虎「技術原因」,讓原定於明天與觀眾見面的FIRST影展閉幕電影《寄生蟲》取消放映。
西寧是座魔幻的城市麼?
答案是肯定的。在新崛起的商區唐道637,胡歌的微笑(當然是海報)在風中搖曳,隔壁就是蜀味鴨爪爪火鍋店的招聘廣告;熱褲辣妹與包裹得嚴實的僧侶擦肩而過,一旁大媽們跳著頗具藏族風情的廣場舞;如果此刻你抬頭,青海天空上方的雲就像皮克斯動畫一樣夢幻飽滿。
但今年FIRST影展卻更加接地氣了,超過7成的項目已經擁有資方和製片團隊,展映單元的策展主題被定義為「敘事現實」,產業放映和創投會成了創作者與市場代表最直接的溝通平台,共識正在逐漸形成:電影的藝術性與商業價值並非此消彼長,曲高和寡的形容被受眾細分取代,再說了,誰說作者電影就不可以是叫好又叫座的作品?
不止影展,年輕一代的創作者們也在發生變化。與前輩們相比,接受過良好教育、擁有更廣闊視野的青年導演不再描摹苦難,而是通過記錄大時代中的個體命運,去試圖解讀當代中國的人際關係。
是「對話」不是「喊話」,正讓FIRST影展在探索一個健康電影市場的多樣性之路上,走得更遠。
「我覺得我不是在FIRST,而好像在蘋果發布會」
「史上最強片單」,是不少影迷和從業者對本屆FIRST競賽單元作品的初印象。
幾萬塊錢拍出的質感粗糲的獨立電影少了,擁有製片團隊和投資方的作品在FIRST征片名單中高達71%。主競賽單元的電影不乏明星光環保駕護航,比如《春江水暖》的音樂總監是竇唯,《春潮》和《馬賽克少女》背後有郝蕾、金燕玲、王傳君與王硯輝等演員加盟;而汪涵監製的《第一次的離別》,背後整整齊齊碼了9家出品方。
即便是像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這種導演自己掏錢開拍的小片,也通過平台創投找到了合適的投資方與後期團隊,由饒曉志擔任監製。隨著電影市場環境與製片環節的日趨成熟,正如影展組織不斷完善一樣,在這屆FIRST影展上我們目睹了中國新一代青年導演作品,由草莽式發展走向更為精細化運作的工業系統,影片的質量整體高於往年。
百花齊放一直是FIRST的優良傳統,今年更像是一次國家地域文化大穿越的見證:《春潮》與《慕伶,一鳴,偉明》讓觀眾意識到東北與廣東家庭關係的迥然不同,《魚樂園》講述北京爺們兒不停換「嬸」的經歷,《世外桃源》營造了重慶餐廳洗腦騙局,人們沉浸在《春江水暖》描摹的繾綣水鄉市井生活長卷中,也在《第一次的離別》里體味到西北邊疆藏在豐茂草原深處的詩意與柔軟。
來自河北衡水的《夏洛克》導演徐磊同一天看了《慕伶》與《春江水暖》,「我挺震驚的,導演30歲出頭就能拍出這麼成熟的作品。另一個深刻感受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真是不一樣的動物,他們的情感太細膩了,對比之下我們就太糙太直男了(笑)。」
一位製片人則向拍sir直言今年的片單有收穫驚喜:「今年的院線電影很少有特別真摯的作品,但在FIRST卻能看到不少,感覺青年導演們更成熟了,也更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。」
資本的湧入與市場化帶來哪些變化?在FIRST創投會現場,「錢」成為評審與創作者交流不可迴避的問題,「300萬的預算有點吃緊?」、「有明確的電影節推廣設想嗎?」等此起彼伏。一些項目已經擁有了完整的製片和宣發思路,一些則碼好了演員與主創陣容,還有評審看中編劇口若懸河的能力,建議其不如開個直播安利自己的長篇故事。
「我覺得我不是在FIRST,而好像在蘋果發布會,」一位評審說。
有人對這種變化表示了擔憂。一位青年導演認為,獨立製片的消失是今年FIRST比較明顯的變化。「一直以來獨立電影都缺少媒體空間和放映空間,帶有獨立電影性質的影展只有FIRST還在做。錢多了是好事嗎?我覺得這東西是相輔相成的,當你可以找到更多錢,更多的慾望和目的也會隨之而來。」
我們最直接的感受是,和商業市場上的導演們一樣,年輕導演們開始要求採訪看稿,一些涉及投資或內容的敏感問題被謹慎避開。
「我沒關係,但怕影響背後出品方,」他們坦言。
市場變化也在無形中影響著年輕導演的創作方向。近兩年現實題材電影開始叫座,各大片方也拋下魔幻IP,開始新一輪對真實事件改編和非虛構的爭搶。而年輕導演基於人生閱歷的單純,頭幾部作品創作往往不會脫離家鄉和自身生活,自然也成為片方追逐的對象。
但取材現實就一定是好的麼?FIRST影展評委會輪值主席刁亦男認為,部分年輕導演對於現實題材的創作仍停留在模擬現實的階段。「在後面的創作過程中,他們需要通過想像力來跨越完全靠自身經歷的闡述,用更多不同手段達到內心想要訴求的東西。簡言之,從生活當中截取原材料,把它孵化和釀成他想要的那杯酒。」
FIRST評審、著名編劇述平則表示比起個人經驗的真實表達,他更喜歡從地面起飛的作品,「這屆作品中似乎沒有看到。」不過令他欣慰的是,這屆電影節影片還沒有直奔商業而去,都是在自己的敘事狀態里堅持原有的想法。
目的性過強,也可能導致不必要的激進。在FIRST放映的頭幾天,FIRST聯合創始人李子為一番關於競賽片豆瓣評分不應低於6.5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。李子為的出發點當然是維護年輕導演,畢竟在口碑至上的今天,評分完全有可能影響影片後續市場發行表現。
但誰又能取代觀眾的投票權呢?後來在另一場放映前交流中,李子為坦言回去後被同事拉到房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批評教育。雖然脾氣是改不了了,但她選擇放權,「電影就是電影,而世界上最偉大和最正確的是時間。」
「記者之眼」與貼地飛行
FIRST還能「撒野」麼?
「電影節的好壞以及未來如何,只有一個評判標準,就是它的片子怎麼樣,」今年首次擔任FIRST競賽單元評審的秦昊認為。
平心而論,本屆FIRST影展的片單並未令人失望。貼地感是強烈的,城鎮拆遷,父母贍養,新聞公正,民族兒童教育甚至新農合成為年輕導演們關注的議題,用鏡頭記錄時代變遷,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社會裡的迫切使命。
「所有人包括我們自己每天都像過山車一樣,過著沸騰的生活。對創作者而言這是很好的時代,你有講不完的故事。」《春潮》導演楊荔鈉認為。
年輕導演頭幾部作品的創作往往更依賴於個人經驗,比如《春江水暖》中三位小輩,就分別代表了導演顧曉剛對於年輕一代家庭觀念的變化:有離開故鄉試圖對抗系統的海歸派,有接受和認同家族的小鎮青年,也有曾經叛逆如今與家人和解的轉變者。
一個頗具玩味的現象是,當導演們希望藉助影像來洞察人與社會、人與人的關係時,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記者尤其調查記者的角色:在《馬賽克少女》、《春潮》或者《送我上青雲》中,通過記者的視角觀眾會瞥見那些大時代滾滾車輪下,被日常忽視的部分。
比如被捲入重要事件中的個體命運。《馬賽克少女》放映結束後,部分觀眾認為電影前後割裂、像是《嘉年華》 《狗十三》的合體,結局也分外迷離,導演翟義祥並不感到意外,也願意讓電影進入更廣泛的討論空間。
「產生斷裂可能是因為不太習慣,」他告訴一起拍電影(ID:yiqipaidianying),「大家可能把它當做特別敏感或特殊的題材,但影片最後討論的方向卻是事件以外,人與人之間關係或者人性多重角度的審視。(性侵)事件發生後,所有影響作用到女孩身上,大家都在追尋事件真相和反轉,等待一個結果。就不能盯著人看,理解她的處境麼?」